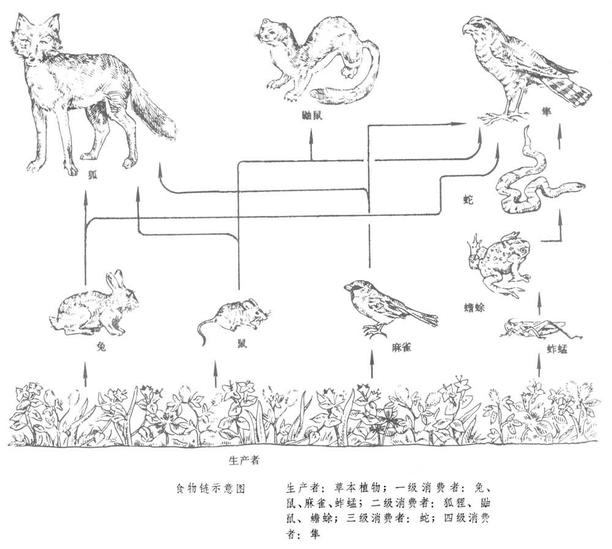利益与共论
承认保存企业营运价值的必要性,还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经济上的合理目标。在法律基于种种理由而必须保留破产清算制度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合理目标,必须采用一种能够促使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自愿选择以保存企业营运价值的方式行使权力的产权安排。换句话说,如果被保存下来的营运价值仅仅属于债务人而不能使债权人受益,或者说,如果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只能寄托于企业资产的清算价值,那么,毫无疑问,债权人宁可选择清算分配。因此,法律制度需要作出一种安排,以便使债权人成为保存企业营运价值的第一受益者。这意味着,法律应当使债权人成为重整企业的事实上的所有人,从而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使他们共同致力于拯救企业的过程。
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与共关系,一位叫彼得。戈根的人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讲述了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一个宾西法尼亚州的男孩受到了镇上的表彰,因为他潜入水中救起了他的同伴汉斯,后者是在滑冰时误履薄冰而落水的。当镇长热情洋溢地对这个男孩的超乎寻常的勇敢大加赞扬后,这个男孩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明白你的这番关于见义勇为的废话有什么意义。我当时不能不救起汉斯。他穿着我刚买来的名牌冰鞋。’”在这里,戈根是要把债权人描写成“一个不得不拯救债务人以便挽救自己的贷款的人”。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反过来,把这位救人者看成是债务人也未尝不可,因为,债务人也必须“避免债权人蒙受太大的损失以便保护他自己的生存”。这也许是用了一种最为浅显的方式来解说利益与共理论。 一些学者对利益与共论作出了更为精确的解释。例如,在美国,道格拉斯、贝尔德、托马斯。杰克逊和罗伯特。斯科特都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公司破产和特殊意义上的第11章都应当致力于使那些投资于债务人的人的财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超越破产的概念,法律把这些人解释为有权享有债务人资产的人,并且把这种秩序解释为这些请求权人得以满足的秩序。有担保的债权人首先受偿,然后是无担保的债权人,再后是股份持有者。当一家公司处于无力偿债的状态时,债权人在事实上就是该公司的所有者。上述学者都主张破产程序应当为债务人的所有者的集体利益而起作用。关于债权人对无力偿债的债务人的财产享有支配权的根据,可以用民法上的债的一般担保理论来说明。所谓债的一般担保,是指法律以债务人所有的全部财产来担保债的履行。大陆法上的保全制度(代位权、撤销权)、强制执行制度和破产清算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或者程序,对债务人的财产行使权利;在此期间,债务人对财产的支配权处于停止状态。只有当债权人的债权获得满足时,债务人才能对剩余的财产行使支配权。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则债务人丧失全部财产(此时,倘若债务人为企业,则该企业因失去必要的财产基础而告消灭)。 在破产程序中,法律基于公平清偿的目的,将债务人的财产置于一个管理人或者清算人的掌管之下。管理人根据债权人的集体意志-债权人会议决议或者监督人的指示-管理、处分和分配财产。从本质上讲,此时的财产是属于全体债权人的,或者说,其最终归属一般说来是属于债权人的。 很明显,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利益是排斥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出资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利益相对立和冲突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债权,法律不得不剥夺债务人的现实利益,同时也剥夺了他的将来利益,即剥夺了他运用已有的财产和信誉所能获得的一切。破产人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对于诚实经营而不幸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务人来说,这是一个冷酷的结局,而且,这不仅意味着债务人的牺牲,而且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无论是经营者的个人才能,还是企业的资产组合和无形资产,都是一种社会的资源。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制度补救,现代破产法设立了免责制度,给诚实而不幸的破产自然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免责制度并不能给那些诚实而不幸的破产企业带来“重新开始”的机会。
当然,还有一种较为积极的制度补救-和解。依照和解程序,通过当事人协商,达成关于债务延缓、债务削减以及其他清偿方式的妥协,可能使债务人免于破产倒闭的结局。但是,和解是以债权人的自愿忍让为条件的。在实践中,可能有许多因素使这种条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例如,有担保的债权人满足于由即时处分担保物受偿,债权人急需现金,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未来偿付能力缺乏信心,等等。不可能把债务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利益作为债权人的行为动机。从理论上讲,和解方案如果不能给债权人带来比清算分配更大的好处,债权人不会作出自愿忍让。这种好处一般是指超过清算分配的债务清偿额;而且,这种超过的幅度,应当足以抵消债权人因延迟清偿而承担的风险和损失。此外,由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市场波动等因素带来的财产贬值风险,以及债务人基于自身原因或者制度原因的信用缺乏等等,往往也是导致债权人不接受和解方案的因素。 从产权安排的角度看,在和解成立后破产程序终结的情况下,破产程序对债务人财产的拘束即告解除,债权人依破产程序取得的对债务人财产的支配状态亦告结束,债务人恢复对其财产的支配权。这样,由于债权人依和解协议受偿所寄托的财产掌握在债务人手中,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也就处在某种“任人摆布”的地位。这也是许多债权人对和解存有疑虑的一个原因。 由此可见,传统破产关于债务人财产的产权安排采取的“非此即彼”-即“不是由债权人支配便是由债务人支配”-的方式,终究不能消除破产事件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利益对立与冲突,而困境企业的复兴机会和希望,往往就在这种对立与冲突中失之交臂,从而导致企业倒闭的悲惨结局。
重整制度对债务人财产的产权安排,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产权”的设计。具体说,在承认债务人及其出资人的已有产权地位的前提下,赋予债权人以财产支配者的法律地位。在这种双重产权的情况下,财产的实际支配被委托给一个中立者-法院或者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在重整期间,可以由债务人继续占有财产和营业,也可以由法院任命的其他人接管财产和营业;在重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出资人)都有发言权;除了债权人外,股东有时也享有对重整计划的表决权,或者至少是享有就重整计划的批准陈述意见的权利。总之,重整程序是一个多方协商机制,其协商决定的内容,不仅包括债务清偿方案,而且包括企业复兴方案。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产权地位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双重产权的理论根据何在?产权来源于投资。要承认债权人的产权地位,必须首先承认债权人的投资地位。
投资就是一个财产主体将自己的财产转入另一个财产主体的名下,并于未来获取回报性偿付的行为。由投资行为产生的投资者的回报索取权,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回报,即有确定的偿付金额,并且通常有确定的支付期限;另一种是浮动回报,即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回报,它没有固定偿付额,但有一定的利润分享比例或者分享规则。前一种即为债权方式,后一种则为股权方式。在支付顺位上,前者优先。
由于债权的回报支付是数额固定并且优先于股权的回报支付,相对地说,处于数额未定且劣后受偿地位的股权持有人,对企业的效益更为关心。无论是从利益均衡方面讲,还是从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动机方面讲,都应当安排股权在企业内部事务决定中的优先地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债权在一次或分期取得回报支付后即告消灭,因而债权的生命周期短,流动性大,这与股权的长期存续状态恰好相反。因此,即使主张债权人在企业正常运行情况下享有内部权力地位,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债权人和股东都是将自己的经济资源投入企业的运行,从而获取自己期待的回报;他们的利益都是与企业的兴衰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利益与共的,但是,从分配的角度讲,它们又是利益对立和冲突的。分配冲突在任何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都是不可避免的;股东之间,合伙人之间,同一债务人的多个债权人之间,概莫能外。
由此可见,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况下,如果将有关财产和债权的清理程序设计成单纯的利益分配机制,那么他就不免造成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债权人相互的利益冲突状态,即人人都想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时的企业,好比一匹病马,由于它的主人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利益,它面临着被屠宰分食的命运。显然,要拯救这匹病马,当务之急就是要让这些闹着要“杀马分肉”的主人们冷静下来,多想想他们的共同利益;如果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医治好,那么,大家都会得到更大的好处;按照前面论述的营运价值理论,“马肉”的价值(清算价值)小于“活马”的价值(营运价值),“杀马”造成的价值损失是大家的损失,而“救马”所挽救的这部分价值便是大家的获益。